忘得了前女友,忘不了那碗炒面

左伢的卤鸡腿
左伢是食堂大师傅的孩子,比我大几月,三十多年前,他随母亲来浏阳小住,和我玩了一个暑假。
他长得什么样,我已经记大不清了,依稀记得他瘦瘦的,鼻子上总挂着两条清鼻涕。有时候鼻涕滴下,拉得老长,他头朝后仰,深吸一口,又吸回鼻腔里去。
左师傅家,在食堂后门旁的一间平房里,门前一个小煤炉,灶门关着。那是左师傅夜里烧水用的,左伢母子来了,偶尔也用来炒菜。

©gz.bendibao.com
机关几进几出,好多栋房子,左伢只在这个院子里玩,他父亲交待的,要左伢莫给他惹祸。我看见他时,他坐在家门口的水泥沟边玩,身后一片桔子树,他躲在树荫里。
我凑过去,“你干什么呀?”
他转过头,望着我笑,“烧鼻涕虫咧。”
他的手里抓着一把盐,另一只手拈一小撮,手指轻轻磨挲,细小的盐粒纷纷而下,撒在鼻涕虫身上,鼻涕虫如遭电击,颤抖、翻滚,一会儿,就化作一摊水。
我低头看了一会,觉得无趣。
“打板儿不?”我小心地问。
“来。”他一翻身站了起来。
我家住在院子西头,第二天,左伢吃过早饭就来找我了,我正趴在桌前写头一天的日记,左伢在桌边盯着,左看右看,桌上饭罩下罩着母亲上班前煮好的面条,干拌的,并不想吃。左伢揭开罩子看,“面稠了。”他说。
“炒一下好吃些。”他又说。
左伢开门走了出去,一会儿,又回来了,“用这个炒。”他手掌摊开,掌心里卧着个鸡蛋,左伢母亲带了只母鸡过来,绳拴着,养在家门口了。
他自来熟地进了厨房,拔掉灶门,放上锅,锅热了,才想起问我油在哪。
我俩在厨房一通翻找,找到了陶罐盛的猪油及一干佐料。
左伢舀了一勺猪油,又倒回去一些,浅浅地在锅里浇了一圈,油热了,将鸡蛋敲进去,炒勺稍稍拌炒,将面条倒入,搅散了,不停翻炒,香气逐渐在厨房弥散,我的口水溢了出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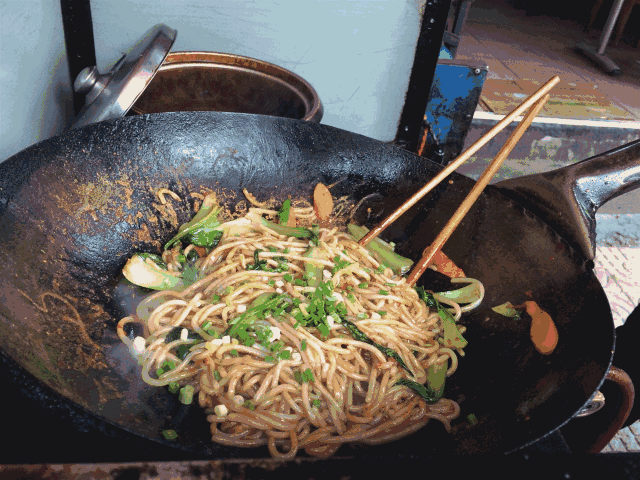
©sohu.com
左伢个子和我一般高,踮着脚,炒得满头大汗。
临起锅时,放一撮碎干椒,翻炒两下,盛碗。
左伢找了个小碗,给自己盛了小半碗,“我早上吃过了,吃一点就好了。”他说。
面很香,我吃得干干净净。
● ● ●
和我在一起,左伢可以出院子。往前一个院子,是孩子们玩耍的大本营,水泥坪里经常堆着一些木头,尖尖的沙堆被雨打湿又被日头晒干,院子的东角上有一个防空洞,北面种着一排柚子树,中间间隔种着两棵香樟,红墙的两层小楼躲在树荫底下,是机关人员办公的一处地方。
孩子们就在院中玩耍,爬上木堆,在沙堆里挖洞,分成两派玩打仗游戏,下雨的日子,大部队转到走廊里,在檐下嘻闹,吵得办公的人出来赶。
左伢很快融入了集体,没几日就当起了孩子王,他力气很大,单手就能把高出一个头的孩子撂倒;又很会爬树,三两下就能爬到柚子树的顶上;各种游戏,他都上手极快,板儿总是他赢的多,玩“江山江切”(一种类似于三子棋的游戏,用小刀在泥地上划出格子,甩刀插格子,插中刀立住,算占一格,占的格子多的人获胜。)几无敌手。我们很快有了一个小团队,左伢对团队的核心成员还有一项福利——偷菜吃。

©dreamkidland.com
左师傅有食堂后门的钥匙,放在家里五屉柜里,左伢知道地方,中午两三点的时候,食堂空无一人,正是潜入的好时机。左伢偷了钥匙,打开后门,三五个孩子一拥而入,在蒸屉里头找菜吃,蒸屉早已断了火,小陶钵一钵钵地装着中午卖剩下的菜,大家一人掏一碗出来吃,肉菜很少,最好的时候,我偷到过一钵火焙鱼,不敢独享,几人分吃了。多是南瓜、酸菜或者甜菜梗,在那个鸡蛋都不能常常吃上的年月,有油有盐的菜对于我们来说,都是好东西。有时候,一个菜咸了,吃完了,得到厨房的水龙头下灌几口凉水。

©szhyxcy.com
菜不敢偷太多,容易露馅,剩菜少,每人吃一钵,剩菜多,每人就吃两钵,吃完洗碗,放好,厨房里干干净净,好像没有人进来过一样。
现今想来,在当时,我们是把偷菜当事业在做啊。
●●●
我们偷菜的事终被发现了,那天晚上,左师傅在家里打左伢,左伢杀猪似地叫,嚎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。
父亲和几个邻居赶过去了,我跟在父亲后头。
待我挤进人群里,左师傅已经被人拦腰抱住了,左伢缩在墙角抽泣,眼神有我从不曾见过的茫然和怯弱,脸上赫然印着个鞋印子。左师傅下了狠手了。
“多大的事,你会把他打死咧。”旁人啧啧地叹。
“细时偷针,大了偷金。”左师傅恨恨说,“一回我就要教他懂,屋里胀不饱,你要偷?”
“我也吃了。”我胀着脸说,声如针尖。
屋内一片寂静。
“我来赔单位上吧。”父亲打破了沉默,面无表情。
“我也要出一半的。”左师傅说。
两人一番推让。
那天回到家,父亲并没有打我,母亲要打,被他拦住了。他跟我说了好久道理,我只听明白了一句,“你这样做,丢我们张家的脸面。”父亲说这话时,神色黯然,好像他赖以为傲的东西,果然被我丢了。
左伢的脸肿了半个月,肿消了,他也要回家了。在那段时间里,他和我格外亲些,父亲和左伢父亲并不禁我们一起玩耍,我们常常出了院子,走一段下坡,去河岸上。左伢做了一个沉网,放上些米饭,放一块石头,沉入水里,捕些小鱼小虾,回来喂鸡。若是鱼个头大些,我们烧红了锅子,干煸了,嘻嘻哈哈地撕着吃,鱼肉香甜,几口就吃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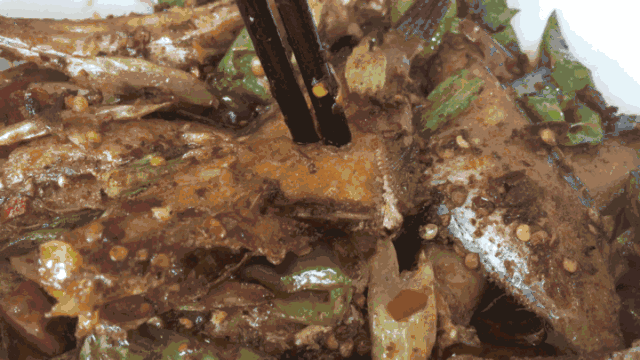
©sohu.com
暑假快结束的一天晚上,正是晚饭时间,我家的门被敲开了。左伢端着个碗站在门外,“我家杀了鸡,送一碗给格胖吃。”左伢说。
母亲让他进来,他端着碗,小心翼翼地放在饭桌上,碗里有一只鸡腿,一个大鸡翅,卤好了,暗沉的肉色,还带着小半碗汤汁,浓香扑面。左伢母亲把那只母鸡杀了。
“好吃咧,你吃咯。”左伢吞着口水,推了一把我,笑着,一仰头,将挂下的鼻涕吸回鼻腔。
“好咧,你吃不?”我问。
“家里还有,我回去了。”左伢转身就走,出了门,消失在夜色里。
那年月,卤鸡是难得的吃食。鸡肉入了味,父母尽着我吃,我抓着鸡腿啃得半天,小心翼翼中带着不舍,骨缝里的一丝丝肉都剔干净了,中间添了几轮饭,卤汁倒出,拌在饭上,大口地扒。

©sohu.com
还碗回去时,左伢迎的我,左伢和母亲已经吃完了,左师傅就着卤鸡喝酒,桌前一堆鸡骨。
“好吃吧。”左伢笑眯眯地。
我点点头。
“来枨冲(浏阳的一个乡)啊,我让我妈做给你吃啊。”左伢认真地说。
“好啊。”我拼命地点头。
第二天,左伢随母亲回去了。不久,左师傅也离职了。
这一家人,我此后再没有见过。

鲁蛋蛋的炒面
鲁蛋蛋的炒面不是他自己做的,夜宵摊点上端的。
鲁蛋蛋姓鲁,是我的初中同学,蛋蛋是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,一直叫到现在。初中毕业后,他去读了职业学校学电脑,我们久未谋面。后来某天在路上遇见,聊了聊,相约吃了顿饭。忽然就变得特别要好,经常约在一起玩。
彼时,我已经到长沙上班了,租住在单位旁,尚不会说长沙话,对陌生的环境不自觉地抗拒。闲时看书、看电视,没有一个朋友。我常常夜间吃过饭,独自走上街,漫无目的地走,路灯下每一条路都寂寥,路上的每一个人都陌生。大约半年多的时间,以滴水井为起点,我的步子丈量了差不多大半个河东,走累了,就坐公交车回去。
那是我最瘦的时候。
那段时间,我每个周末都回浏阳,周五下班去东站坐车,天黑就到了。不急着回家,先去鲁蛋蛋店里报到。
鲁蛋蛋开着个打印社,生意挺好,每回去,他一准在忙,做横幅、丝印,或者印广告单,鲁蛋蛋好学肯钻,设计、制版样样来得,兼之做事精致,为人诚恳,店开得不久,名声就传开了。
看到我来,鲁蛋蛋总说,“等下啊,没空管你啊,自己倒水喝。”
我熟门熟路,自顾去喝水,喝完了再嚷嚷,“我没吃晚饭啊,饿了。”我义正言辞,“冇落屋先来看你,够兄弟吧?”
鲁蛋蛋无可奈何地叹气,打发帮工去买炒面,“我先做吧,你快去快回。”他交待着。
“蛋炒还是肉炒啊,哥哥。”帮工问。
“肉丝蛋炒面,麻烦你。”我说,看着他的背影,问鲁蛋蛋,“新来的?之前那个妹子呢?”

©sohu.com
八点半,正是难找吃的时候,晚餐的点过了,大多数夜宵摊子还没有开起来。买碗炒面千难万难。
有一家夜宵店,开在才常路临河的口子上,晚上开店开得早,离鲁蛋蛋店子也不远,走着来回,不过十几分钟,骑自行车,能更快一些。
帮工把面买回来,塑料饭盒装着,打开来,仍热气腾腾。
那碗炒面份量足,撑得饭盒鼓鼓囊囊。用的碱面,水煮至六成熟起锅过冷水沥干,鸡蛋搭配着瘦肉丝大火急炒,放一勺剁辣椒、少许盐调味,起锅时撒些葱花,咸淡适中,吃到嘴里,尚有几分筋道,搭配着肉的香和蛋的鲜,还有少许面条受热不匀,炒枯了,带着焦香,吃起来又糯又脆。

©sohu.com
一盒炒面扒下肚,扔了饭盒,抹抹嘴,不急着走,打开鲁蛋蛋的电脑,“装了什么新游戏没有?”
在鲁蛋蛋的电脑上,我玩过两款游戏,智冠出的《金庸群侠传》和日版《红楼梦》,都通关了。
游戏玩得晚了,索性就不回家,事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,也不管鲁蛋蛋愿不愿意留我宿。
鲁蛋蛋的电脑换得快,始终走在潮流尖端,我在他家电脑上看了人生第一部DVD电影——《食神》,在他那台装了独立显卡的电脑上,两人坐在拉了卷闸门的店里,对着15寸显示屏,初时惊叹于画质的艳丽清晰,不住称赞,后来被剧情吸引,笑得前仰后翻。

●●●
鲁蛋蛋是个帅哥,唇红齿白,肤白大眼,天生自来卷。他为人温润,兄弟交待的事,总是想方设法完成。我家新买一台电脑,父母不会用,父亲要看股票,常常打电话问我,问得烦了,我就推给鲁蛋蛋,“我交待他了,你问他。”我对父亲说。
鲁蛋蛋服务极好,电话解释不清就上门,兼了免费的软件辅导和硬件维护。偶尔打电话怼我,“背时交了你这个朋友。”
“你是我兄弟呐。”我理直气壮。
后来,另一位同学,钢皮加入了我们,有机会聚的时候,三人一起去老友谊前的夜宵点吃宵夜,卤味、炒菜加炒粉,总能吃个肚儿圆。

©sohu.com
有一回,三人都吃坏了肚子,同时进医院打吊针。
病好了,又相约去吃过。
更多时候,我们点一碗炒面,去鲁蛋蛋店里看片,炒面馆子有外送了,吃着方便。而蛋蛋店里的电脑永远是最快的,画质清晰,立体声环绕,除了屏幕小点,再没有其他可以挑剔的地方。
更何况,还可以吃炒面呢。
后来,我们仨都交了女朋友,再后来,钢皮换了一个,我也换了一个,鲁蛋蛋的女朋友还是那个。那个女孩与他从小玩到大,成长中渐生情愫,忽一日,女孩挑明了。从此,每次鲁蛋蛋出来,都带着她,女孩短发,圆圆的脸,目光灵动,略带些俏皮,唱歌很好听。
后来,我在长沙渐渐交了一些朋友,也就不每周回浏阳了,但每回回去,还是必去鲁蛋蛋店里报到。
某一次,我照例八点半到的浏阳,事先打电话通知了鲁蛋蛋,到时,钢皮早已等在蛋蛋店里,玩着游戏。那天我带着从长沙买的碟片,想叫炒面边吃边看片,蛋蛋非要出去吃,“我请客。”他说。
一路上,鲁蛋蛋神情都是郁郁的,我问钢皮怎么了,“好像是分了,”钢皮说,“妹子父母不同意。”

©sohu.com
那天晚上,蛋蛋喝了好多啤酒,彼时我还不会喝酒,钢皮陪的,钢皮继承了他父亲的好酒量,号称千杯不醉。
酒喝得并不久,我饭还没有吃饱,蛋蛋就醉了,我们拉他回家,蛋蛋不肯,使劲挣脱,手指指到我的鼻梁上,囫囵地骂着,舌头大了,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一向温润的蛋蛋终于露出了狂怒的一面。他拉着我俩在滨河路上乱走,从西走到东,又走回来。他始终不说话,烦躁的神色写在脸上。
最后,大家都累了。我们终于回到了他的打印社门口,蛋蛋左找右找不到钥匙,走到卷闸门前,使劲地捶门,哪里有人呐。我们不知安慰,眼睁睁地看着他捶累了,走到路沿上,一屁股坐下,垂下头,长久地没有声息。近前一看,他趴在膝上睡着了,像一只受伤的猫。
蛋蛋有许久没有找女友,其间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了很多亲,蛋蛋每次都去,见个面,走个过场,从不联系对方。女孩心仪他,给他打电话,他也是冷冷的,过分的礼貌里藏着一块冰。
许久以后,我和蛋蛋穿过步行街去赶个饭局。看到他的前女友和一个男孩在溜旱冰,两人一前一后,追逐着,从我们身边滑过。
“你看见......”我拍了一把鲁蛋蛋。
“我没看见。”他打断了我的话,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去。
从此,我再不提那个女生,以至于后来,我竟忘了那女孩的名字。又过了许久,蛋蛋结婚了。他结婚还算早的,至少比我早,钢皮结婚早过他。大喜之前,我提前去了他家,给他上礼,“终于有人收你了。”我笑他。
“谁来收你呢?”他怼回来,“要等几年噢?”
蛋蛋一语成谶,好几年后,我才结婚。
我和太太回浏阳办的婚礼。事前我打电话给蛋蛋。
“哪个女的瞎了眼。”蛋蛋在电话那头怼我。
距离婚期还有一个多月,鲁蛋蛋找到我的父亲,他给我订制了一批请柬,自己设计的,打印好了,“只要写宾客名字,”蛋蛋说,“也不晓得还能帮什么忙,叔叔有事找我。”
父亲打电话给我,大赞蛋蛋义气。
我忙给他打电话,“帮忙归帮忙,礼金不能少啊。”我说。
“封好了,老大,”蛋蛋嗔道,“三年内离婚还我。”
“快呸掉!”
“呸!”
十几年过去了,蛋蛋家的打印社换了几个地方,蛋蛋的女儿长大了,那家开在离打印社十几分钟距离的炒面馆,我们也很久没有光顾了,听说已经换了地方。
偶尔回家,我们还是会聚,吃饭,喝酒,蛋蛋酒喝得节制,不打牌,但是我打牌,他会陪着,在一旁看手机。
“你这样像我的女朋友诶。”我常笑他。
“呸!”他怼我,跑来翻我的包,“iPod里有新下的片子吗?”
“有一部横山夏希。”
他拿起iPod,熟稔地按开密码,坐到一边去了。

写完这篇文章,我发给蛋蛋看,我发信息问他:“炒面馆子是不是‘杯莫亭(浏阳一家有名的夜宵店)’?”
他说:“是啊。”
我又说:“真是奇怪,我真不记得你的前女友的名字啊。”
他回:“正常,我也不记得你的前女友们。”
半晌,他发来一条信息,“几时回,吃炒面去吧。”
我回:“好啊。”


-

#在家做出五星级牛排#泰式加拿大北极虾蛋饼
加拿大北极虾 面粉 葱 黄瓜 花生碎 鸡蛋 柠檬 泰式甜酱 豆芽 黑胡椒八鲜过海25976 955 -

#本周热榜#杨枝甘露(五星级餐厅配方)
芒果(中个大小) 西米 西柚 牛奶 椰汁 白砂糖再累不要忘了微笑3263 123 -

菠萝咕噜肉
菠萝 里脊肉 青椒 番茄酱 白砂糖 醋 生抽 清水 水淀粉 油 盐 胡椒粉 红辣椒安浠雪10365 620 -

原味玛德琳
鸡蛋 糖粉 泡打粉 黄油 低筋面粉我要吃饭啦MM2246 75 -

#打工人的健康餐#奥尔良烤翅
鸡全翅 新奥尔良烤肉料 水 生抽 蚝油爱做饭的小猪+3899 102 -

捞汁芦笋
珍选捞汁 芦笋 蒜,小米辣珍选捞汁1539 56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