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吃邻家饭的时代结束了
小时候,邻居家的餐桌无论多小,都能临时加塞一个爸妈因工作而无暇顾及的我。那时候去邻居家蹭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如今在城市里的我们,和邻居的关系,却大都只是在饭点准时闻到隔壁飘来的炒菜香了吧。 今天分享三个跟邻家饭有关的故事,希望也能勾起你的回忆。


我妈把我胳膊差点拽断那天,桂大妈正坐在廊檐下吃臊子面。
那是六岁的我从没见过的一碗面。一只深瓷的大碗里,细白而长的手擀面卧在深红色的辣油汤里,汤里浸着石榴子大小、炸得脆黄的豆腐丁,菱形的明黄色的鸡蛋饼块,橘红而软糯的胡萝卜丁和乳黄色沙绵的小土豆块,汤上还飘着一层切得细碎的翠绿色蒜苗叶。 桂大妈搅了一下面条,一股醋香混着辣椒与杂蔬的味道就飘散在廊檐下了。

那是九十年代初西北小城的夏天,强烈的太阳光把大杂院屋顶的青瓦烤得泛起白光。中午时分,人们总是喜欢敞开大门,在廊檐下活动。
桂大妈一家三口人挤在前院一间十八九平方的小屋里,没有厨房,平时就在屋里支起一只火炉做饭。
夏天,火炉移到了廊上,桂大妈就坐在一只仅能承载她屁股一半大小的木凳上烧火,天更热的时候,就只穿一件洗得有点透明的白色背心,坐在凳子上择菜,随着胳膊晃动,两只布袋一样的大奶就在胸前荡,身下那只细脚伶仃的木凳子“咯吱咯吱”一直叫,好像在喊“救命”。
小时候,我对桂大妈的那只小木凳一直怀有一种近乎兄弟手足般的天然同情,是因为我多少也可算作她巨臀的“受害者”。
大杂院前后院共用一个没有门的、黑乎乎的茅厕,有一次我正在上厕所,桂大妈突然急吼吼地冲了进来,看也不看,脱了裤子就蹲,一屁股差点把来不及反应的我怼到茅坑里。 我急得忙扯住她的衣服,桂大妈“啊”的一声大喊,回头看见是我,忙叫道:“哎呀!这个娃咋一声都不吭!”我尴尬至极,提上裤子扭头就跑。
此后每次桂大妈看见我都要说一遍:“哎呀,一个女娃娃,一点声音也没有!下次你见我进厕所,你就大声喊!”
我点点头,继续不吭气。
桂大妈教给我的道理,我似乎并未学会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每次去前院上厕所经过桂大妈的屋子,我都要蹑手蹑脚地窥探一番她的活动:如果她正在做一些一时甩不开手的活,我便把心沉到肚子里,摇头晃脑地上茅房了。
夏天那个中午,我上完厕所,经过桂大妈家时,却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——她手里端了那样一碗深红、喷香的辣油蒙盖的臊子面,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。
臊子面是西北人们常吃的主食。从前没有冰箱,肉类不易保存,每天吃鲜肉不切实际。就买来五花肉,切成小块,在油中不断翻炒,加入酱油、五香粉,老姜,料酒等佐料,直到把五花肉里的油脂全部炒出来,做成臊子,封进一个瓷坛子,油脂漂在上面,遇冷就结成一层光滑的油皮,把炒成褐色的肉牢牢封在下面。这样便可以储存很久。

每逢炒菜、做面,就从坛子里舀几勺,让人们尝尝肉味。而穷人们,连肉也常常吃不起,平时就只能用豆腐、胡萝卜等蔬菜混合炒在一起做面,最多加个鸡蛋饼,这样的面就有了另一个名字——素臊子面。加更多的盐、醋、辣椒,吃的时候大汗淋漓,也很爽快。
桂大妈端着这样一碗素臊子面,叉开两腿坐在廊下的小木凳上,肉山一样,颇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大将风范。
她不断地搅着又长又细的手擀面,那香气直冲进我的鼻孔,让我挪不开腿。她大概也被面香全然吸引,并没有注意到我。
她“哧溜”吸一口,我就咽一下口水,往前溜几步。她再吸几口,我就趁机再往前挪几步,最后差不多都来到了碗旁边,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。
桂大妈这才抬起头看见我。笑了,大声说:“来,娃吃一口!”
说着,筷子夹起一束雪白的面条塞到我嘴边。我拿出吃奶力气,“哧溜溜”狠命吸进嘴里,面条的韧劲带着辣椒油的香气,连同鸡蛋饼的鲜、土豆的沙,醋和蒜苗的尖锐混合起来,六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交响乐,只觉得嘴里好像有很多食物一起在唱歌。
我一边拼命地咀嚼,一边眼睛还斜睨着桂大妈碗里的面条,生怕她吃完没有了。桂大妈又吸了一口,看见我的样子,噗嗤一声笑了,“哎呀,看把娃馋得啊——” 说着又喂给我一大筷子面条。
就这样你一口,我一口,我和桂大妈分享了她的一碗面。眼看着白面条没了,可我还是站在那里,眼巴巴的,等着。
桂大妈明白了,我这是等着喝臊子汤呢。小城风俗,臊子面面条吃完后,汤不能倒,留着盛下一碗面条,喝汤是结束吃饭前的最后一件事。
“娃要喝汤?”她笑着看看我。我点点头,还是不吭声。
桂大妈把碗倾斜着放在我的嘴边,碗太大,我的脸都差点栽进汤里,我感到嘴唇上沾了一层辣椒油,那汤又热又辣,却美味至极。
正沉醉其间,突然耳朵被人提住了,转头就看见我妈气呼呼地瞪着我。她一把揪住我的胳膊:“走!吃饭的时候不往自己家里跑,跑到桂大妈家里要饭吃!”

“你看你把桂大妈的饭都吃光了!”我妈拽着我的胳膊,使劲把我往后院拉,可我就是不想走,我还要喝汤呢,我不能走。于是我顺势蹲在地下,就这么赖着。
桂大妈见状,忙放下碗,“小娃娃吃一口,能吃个啥?”她拽着我的另一只胳膊,把我往她怀里拉。她那圆乎乎的身躯,此刻好像是一只温软、巨大的肉包子。
我妈这时反倒更用劲了,我感觉自己的胳膊都要被扯断了,她一边扯一边说:“走!不能给她惯这个毛病!还寻着吃!一点礼貌也没有!”
那天的拉锯战最终以我妈把我连拖带拽拉回后院才结束。我边被拉扯着,边依依不舍地、不断回头朝桂大妈看。

“小娃娃能吃个啥?”桂大妈站起身子,也往我这边看,愤愤不平地不断重复着这句话。
回家以后,我爸也狠狠批评了我。我这才知道,我这样摸着饭点,专门在邻居家混吃喝的,竟在我们方言里有一个专有词汇——“寻着吃”,短短三个字,发音很是凶狠。可见我并非无赖第一人。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每次和妈妈经过桂大妈门前,桂大妈总是大声对妈妈说:“下次你让娃在我这里吃!这娃心疼啊,平时乖得一点声音也没有!一个娃能吃多少?”
我依旧不说话,就看着桂大妈。
可自从被批评之后,我就再也没有在桂大妈家里寻着吃了。有几次我经过她家廊檐,看见她手里端着碗色彩鲜艳的烩菜,菜上还架着她新蒸好的雪白松软的馒头,就止不住地口水横流。六岁的我那时必须强烈控制自己盯着烩菜看的念头,飞快地,小贼一样从她身边溜走。

那时的我毫不怀疑,桂大妈家的烩菜是我所能想到的至尊美味,她家的馍肯定也是举世无双。许多个下午,当院子里来了衣衫褴褛、要馍吃的老乞丐,桂大妈总是从箩里摸出两个刚蒸好的雪白大馒头。

老乞丐就把拐杖立在廊檐的柱子旁,黑糊糊的双手捧着馒头,颤巍巍地坐在桂大妈让出的小木凳上,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咀嚼着馒头。桂大妈就像当初给我喂饭一样笑着,手里捧着一碗茶,伏下身子大声在老乞丐耳边吼:“老人家,喝茶,小心噎着。”
每当这时,我总在墙背后偷偷看老乞丐一边吞咽着桂大妈的馒头,一边老泪纵横,看着看着,竟然对他也有些羡慕了。

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,几乎每个周末下午四五点,张婆婆总要在家里“炼臊子”。
一到那时,她就拿出家传了不知几世的、黑黝黝的大铁勺,把臊子放进勺子里,直接放在火上炙烤。等臊子白色的油脂变成了液态,栗色的肉粒也“咝咝”微炸着,颜色变得越来越深,空气里就飘散着混合着了八角桂皮的酱肉香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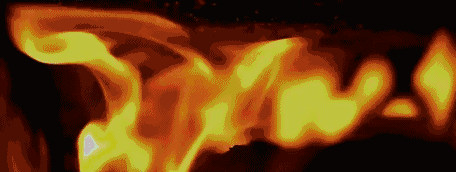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这时,院子里的大人们就耸耸鼻子,叹一声:“啊呀,张妈家的臊子真香啊!”住在她家对门的我闻到了,就像猫闻到了小鱼干,一个激灵站起来,不由地朝她家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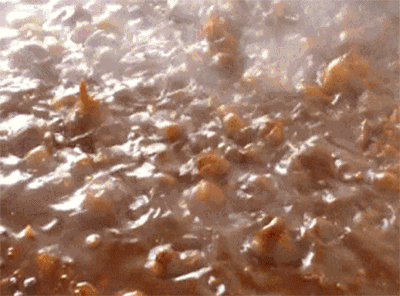
臊子炼好后,张婆婆就从厨房拿出一只大白馒头,一切两半,小心翼翼地把臊子一勺一勺地夹进馒头里,然后便在院里呼唤她二外孙的小名。二外孙看见了,连忙欢欣雀跃地蹦过来,一把捉住馒头,狼吞虎咽起来,臊子油顿时沾满了他的嘴唇,蹭到他粉扑扑的圆脸蛋上,还从他胖胖的手指缝里滴下来。
张婆婆这时总是微笑着弯下腰,轻轻擦去外孙脸上的油。然后怜爱地看着他,嘴里时不时地自语着:“哎呀,我的娃吃得心疼啊。”
张婆婆总是这样看着,我却从未见她自己吃过一口。
张家住在后院,有四个女儿。一到周末,女儿们纷纷带着丈夫孩子回娘家,张婆婆便为全家聚餐忙前忙后,高兴得一刻都停不下来。而女儿们也是各有分工:择菜、揉面、聊天,嗑瓜子。
童年的我常常盼着张婆婆家的周末,只要她女儿一回来,就必然带着外孙,我在院子里就能多几个玩伴。每当家里人手多的时候,张婆婆也一定会做出一些复杂、别致又美味的小吃,也必会送给我家一碗。
春天几场阵雨后,她早早奔向了菜市场,去挑选农民刚摘下来的、最新鲜的苜蓿。 在我的家乡,苜蓿是山野间常见的野菜。那种大叶子肥厚又旺盛的,叫马苜蓿,是牲口的美食,而叶子椭圆而小,害羞地折起来,像汉服的领子一样的苜蓿,是人的吃食。
雨水旺,苜蓿就长得长,农民仅掐一、两寸的短茎,装到尼龙袋里在市场门口贩卖。张婆婆每次都要买上好几斤,在她家银光闪闪的大铝盆里一遍遍淘洗,倒去水,趁着菜潮湿的时候,把每根苜蓿茎都裹上面粉,然后上锅蒸了。苜蓿蒸好后,把味道浓烈的春韭切成一寸长,再挖一勺臊子,将三者放入油锅中同炒,只需加盐就能出锅。

苜蓿饭炒好后,张婆婆总是拿出她家那只嫩绿色的,又深又大的搪瓷碗,高高地满上一大碗,笑盈盈地端到我家里来。一碗粉绿色的苜蓿混着深绿的韭菜叶,间以暗红或栗子色的肉臊,仿佛端来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等到夏季,天气一热,张婆婆的女儿们便忙活开了。
张婆婆先把金灿灿的玉米粉徐徐撒入开水中,边煮边搅拌粘稠的玉米糊,再将玉米糊一勺勺舀入一个更大的黑色陶土多孔漏勺,一个女儿端着漏勺,另一个则要在漏勺下方放一大盆凉水。漏勺里的玉米糊从孔里钻出后,就变成一条条长着小尾巴的金黄色面鱼,纷纷落入凉水里。吃的时候,捞出面鱼,拌以素臊子,还要加上蒜泥,醋等调味品。

当然,吃面鱼最重要的便是油泼辣子了。每当这时,张婆婆的小女儿必定放下手中的瓜子,自告奋勇去烫辣椒。她嗜辣,也独有经验,烫出的辣椒色艳味美,四姐妹无出其右,后来,她真的专门开店去做麻辣烫了。
面鱼一做好,张婆婆就又拿出了她家的嫩绿色大碗,第一碗舀给我家,金黄色的面鱼又细又长,卧在素臊子汤里,油辣椒一大勺放在一边,是为了照顾爸爸不吃辣的口味。每次妈妈拿出小碗匀给我面鱼时,总要叮嘱我:“慢慢吃,别呛着,别呛着!”我瞪着眼睛一边看着妈妈,一边把一条条面鱼飞快地滑进嘴里,根本来不及多想。
秋天一到,新洋芋就下来了。张婆婆山上的亲戚会背一大袋黄澄澄的、乒乓球大小的洋芋蛋下山来看望她。亲戚走了,张婆婆便用它们来做洋芋叉叉。
张婆婆的洋芋叉叉根本不用把洋芋切丝,而是切成小粒,裹上一层面粉,在一个小竹箩里一边撒面粉一边轻摇,直到一粒粒洋芋变成小象牙白色的球体,然后上锅蒸熟,在胡麻油里就着葱花一炒,洋芋饭就成了金黄色的小圆球。
而这圆圆的黄金洋芋饭,这种我与她外孙们都喜欢的可爱吃食,却是我与她家一年里同吃的最后一餐。漫长的冬天一到,西北小城的寻常人家就只能吃洋芋、胡萝卜和菠菜了。天更冷时,张婆婆会挂上一个厚厚的毡布门帘,在屋内生着火炉,女儿们也纷纷窝在自己家里,来得次数也少了。
一个冬天的下午,爸妈出门购物,把我一个人留在院子里和张婆婆的外孙们玩耍。玩着玩着,天就黑了,还飘起了雨夹雪。伙伴们玩饿了,纷纷回家,偌大的院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百年老屋黑乎乎的,我站在花园的冬青树旁,不敢盯着暗处看,也不敢进自家的门,只能眼巴巴儿地望着张婆婆家的玻璃窗,看那里透出的暖黄色的光、凝结在玻璃上的白色水蒸气,以及屋内人影晃动的斑驳。那里有温度,香味,笑语,美食,而我却冷得发抖。

爸爸妈妈去哪儿了?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?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我越来越冷,也越来越害怕,脑子里禁不住开始胡思乱想:他们是不是半路遇到了强盗?遇到了车祸?或者——他们会不会永远不回来了?
突然,一个声音传来:“你爸妈还没回来吗?” 抬起头,张婆婆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。
我忙点点头。
“哎呀我的娃啊!”她连叹一声,“那你来婆婆家,站到外面冻死了!”
我走过去,她掀开门帘,屋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进了屋,张婆婆正和大女儿在方桌上吃饭,一盘土豆丝,许多牙锅盔,摆在桌子上。她的外孙早已吃完了,在床边玩耍。 张婆婆一把把我拉到火炉边坐下,回身取了一牙锅盔,一切两半,把他家盘子里的酸辣土豆丝一筷子一筷子夹在锅盔里,然后递到我的眼前。

“娃饿了吧?快吃!”
土豆丝醋香扑鼻,锅盔两面烙得焦黄,那皮一定是酥脆的,那芯也一定是松软的,而我拼命地咽着口水,忍住不去看它:“我爸妈不让我在外面吃……说是我寻着吃呢。以前我吃桂大妈的饭,他们就把我骂了一顿。”

“哈哈”,张婆婆大笑起来,“哎呀我的娃啊!你别害怕,有张婆婆哩,你爸回来了我给他说。
我看着她,她的笑容那样笃定。
“赶紧吃!”她把馍塞到我手里。我接过来,像她的外孙一样狼吞虎咽起来。这个馍,配以又细又脆的土豆丝,与张婆婆先前送给我家的吃食相比,算是最普通的了,可它对我来说,竟真的是一年里最好吃的。
我饿得慌,吃得狼狈,脸上都是土豆丝的痕迹,湿嗒嗒的。
张婆婆笑眯眯地看着我:“哎呀,我的娃吃得心疼啊!”说着,就弯下腰,轻轻擦去我脸上蹭的油渍。可我却再也忍不住,“哇”得一声哭了。

小的时候,在大杂院里,因着明里别家送的和暗地里寻着吃的,我几乎吃遍了前后院。而这吃遍全院的殊荣,在长辈之中,恐怕也就只有罗婆婆享有了。
罗婆婆很老,据说她和我的曾祖母一样,都出生于晚清时代。曾祖母去世时,我尚未出生。而到我六岁时,罗婆婆还一直都在。曾祖母的遗像挂在我家正墙上,照片里的她居然和罗婆婆有几分相像,所以童年的我总是想不通,为什么罗婆婆住在隔壁,我家却要挂她的照片。
而我同样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:罗婆婆的脚为什么那样尖、那样小,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。
不管天气多热,她总要穿一件宽大的斜襟黑色褂子,阔腿束脚黑裤,一双黑色布鞋,又配着白色布袜子,似乎故意显耀她双脚奇迹般地小。我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走路,生怕她翻个大跟头,又怕一起风,她宽大的衣服充满空气,使她像热气球一样腾空飞走。
后院住的三家人,都是子孙众多,可罗婆婆却只有一个养女,还出嫁得早,隔好几个月才来看她一次,给她留点生活费后就走。
罗婆婆还有一个远方的侄子,也是大半年才看她一次,每次侄子一来,罗婆婆就好像变了一个人,精神焕发,笑容也多了。侄子一走,她就又老了,家里也恢复了原貌,两扇门敞开着,即使人在里面,也没有声音,苍蝇明目张胆地飞进去,又百无聊赖地飞出来。

到了傍晚太阳一落山,罗婆婆就把房门关上睡下了,连灯也不开,后院三面房屋皆灯火通明,唯有南房是沉郁而寂静的黑夜,好像根本没有人住过。
而罗婆婆家黑夜的宁静,第一次被打破,据说是因为我家的一个“吃货”,那还是七十年代的事情。
吃货名曰大黄,是爸爸小时候养的一只大猫,通体金黄,头又圆又大,好像一只小老虎。还没长大的时候,就常和爸爸打架,长大以后,更是夜不归宿,每晚在房顶夜巡,早晨准时从房上跳下来。
老了以后,据说通了人性,每次回家,都不空着爪子,而是带回些小礼物,有时是一只死鸟,有时是死老鼠,潇潇洒洒丢在厨房门口,好像在说:“喂,赏你们吃!”俨然一副大爷风范。
一年腊月,曾祖母早起,突然发现厨房案板上多了只猪耳朵,在那个年代,穷人攒足了劲儿,每年也就是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。猪耳朵即使算作猪肉最便宜的部分之一,也是稀罕物。曾祖母正纳闷是谁好心送来的,突然听到隔壁罗婆婆哭喊起来:“哎呀,我的耳朵咋没了?我的耳朵咋没了?”
这事不消说,定是大黄干的。它大概和我一样嘴馋,也觉得邻居家的饭就是好吃,但它显然比我更勇武,脸皮也更厚,胆敢深夜飞檐走壁潜入邻家,用头轻轻抵开柜子,把罗婆婆放在碗里准备过年的唯一一块肉叼回来。
在罗婆婆的哭喊中,曾祖母忙叫爸爸送还了猪耳朵,被偷了吃食的她还惊魂未定——这一口肉,可是穷人一年的盼望。
大黄自然被曾祖母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当然,这恐怕也有点“杀鸡给猴看”的意思,至少这样的教训对我爸是有用的,那些后来他责怪我“寻着吃”的话,没准就是来源于此。

▲ 图片来自电影《我们俩》
大黄一偷吃,罗婆婆家里的情况就完全暴露出来了。自此,领居们平日给罗婆婆送饭,便要更加贴心。
很多年来,大杂院的老邻居们一直保持着送饭的规矩,就是要知道自家送饭的碗什么时候拿回来。
有时,邻居会当场把碗洗干净,在里面盛上新得的时鲜,让送饭人拿回家。而有时他们会恳切地说一句:“你家的碗过几天再给你送来。”这时,送饭的人要么据理力争,坚持当天拿回,要么心知肚明,点头离开,隔几天,邻居一定会在碗里盛一碗自家用心做的饭还回来。
邻里间的送饭,不论频率如何,总是有送有还的——“来而不往,非礼也”。而那些送饭的人,常常是家里的小孩,他们也就在关于还碗的欲拒还迎的说辞、甚至抢碗的假性扭打中,学会观察、辩论、酬答、博弈甚至角斗。
一碗饭就是一本做人礼仪、体面和人情社会生存法则的教科书。
等我到了能出去送饭的年龄,爸爸是这样教育我的:给罗婆婆的饭,要绵软,因为她年龄大了,牙不好,硬了怕咬不动。去了她家,也一定要看着她把饭倒进自己的碗里,然后把我们家的碗拿回来——不管怎样,都要空着拿回来。

原因是,罗婆婆年纪大了,不能让她劳累洗碗,更不能把碗留在她家,让她破费来还饭。于是,六岁的我把饭往她家碗里一倒,撒腿就跑。罗婆婆这时迈着两只小脚追到门口也追不上,就站在门槛边,扶着门框,嘴里叨叨着:“哎呀,看这个娃,看这个娃……”
张婆婆也常常给罗婆婆送饭,她告诉我,给罗婆婆送饭,一定不能用她家嫩绿色的搪瓷大碗。罗婆婆吃得少,送多了吃不完。更重要的是,一定要看着她吃,因为罗婆婆觉得饭好,会舍不得吃。送来的饭一天天精心保留着,可她家没有冰箱,一顿饭放馊了也舍不得倒,最后就会吃坏身子。
而桂大妈给罗婆婆送饭的规矩更加直接,她看到罗婆婆来前院,就把她留在廊上,亲自盛一碗饭端给她,当场和她一起热乎乎地吃掉。
就在邻居一碗碗饭的来来去去中,罗婆婆越来越老,也渐渐没劲儿和我们为碗的去留问题博弈了。曾祖母去世后,她成了全院最老的人,而随着我的长大,巷子里生于晚清的老者们也一个又一个地逝去了。罗婆婆的同龄人越来越少,她就更懒得出门了。就连六十多岁的张婆婆,在她眼里都是小孩。
只有在张婆婆问她古今之事时,她的眼里才散发出光明:“民国十年大地震的时候呐,我正在厨房炒菜呢……”她的话一下子就多起来。
有一次,我端了一碗饭去她家。她收好饭,似乎无以酬答,一把拉住我的手:“来,罗婆婆看看你的命。”
我好奇地很,跟她坐在床沿上。她戴上眼镜,抚摸着我的手心,默默地看着我的掌纹,一边看一边叹息:“哎呀,这个娃以后,也就像电线杆上的燕子一样飞走了,飞得远得很呐!”
我不信,大声说:“我不走,我爸我妈还在这呢。”
罗婆婆看着我,嘴里念叨着:“我的娃啊,你以后要是有良心,就把你爸你妈接走跟你一块过,要是没良心,就让他们像婆婆一样,老死在这个院里……”她的声音暗下去了。
不久以后,罗婆婆病了。不知是什么病,就是每天卧床,起不来了。这一病,罗婆婆的女儿侄子更是不见踪影,每日三餐,都由邻居们送了。
张婆婆每次熬了稀饭端进去,一进去就是半天,出来后有时候叹着气,有时候抹着眼泪。
桂大妈也端饭进去,出来以后,爱说话的她也不言语。
送了没几天,一个清晨,张婆婆又像往常一样给罗婆婆送早饭,回来后不久,罗婆婆家就变了。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大汉,在她家拉了好几根电线,还换了盏瓦数极大的电灯,光明四溢的,一下子照亮了南房——罗婆婆一辈子都没有开过这样亮的灯。她家家门也敞得更开了,许多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陌生人一个个接踵而至——她家也从没有这样热闹过。
这一天,罗婆婆死了。
我一直以为,罗婆婆正如自己所言,“老死”在院子里。
可不久以后,我却偶然偷听到张婆婆与其他人的悄悄话——罗婆婆是自杀的。那个令罗婆婆卧床的病,其实不过是一场普通感冒,而真正要了她命的,却是对邻居三餐照顾的无以回报。

年老的她唯一能做的,就是以自己的死亡来结束带给邻居的负担。在这个世界上,她再也不想麻烦别人了。
再后来,张婆婆也死了。桂大妈得了糖尿病,瘦得跟麻秆一样,整日守卫在自家违章新建、谋求更多拆迁面积的楼上。就连那单纯要一口馍吃的老乞丐,也不知怎么消失不见了。
我果然如罗婆婆所言,飞得很远很远,搬过许多次家,有过许多邻居,他们中很多人房子明亮,车子气派,比我儿时的邻居富有千百倍,可他们的门户一直是紧闭的,别说分享一顿饭食,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
而现在,我也关紧了家门,心变得越来越硬。
大杂院要拆了,老邻居也一个个没有了,邻家饭的味道彻底消失不见。现在的我,还是不明白,究竟是时代带走了我的邻居,还是他们的死亡和离散,最终结束了一个人与人之间诚恳、礼让而又温情的时代?

互动
你吃过邻家饭嘛?
告诉我们你关于邻家饭的回忆。










-

素菜也可以很美味~豆豉油麦菜
油麦菜 豆豉 蒜 葱 小米辣阳阳妈的烹饪日记4176 139 -

#打工人的健康餐# 蚕豆焖肉丝
蚕豆 肉丝 红辣椒 大葱美美生活小能手28531 1092 -

低脂营养凉拌菜:木耳拌腐竹
木耳 腐竹 酱油 蒜泥 油 醋 糖 耗油 小米辣茉茉20165840 180 -

#打工人的健康餐#凉拌风味鹌鹑蛋
盐 黄豆酱油 生抽 糖 鹌鹑蛋 老抽 洋葱丁 蒜末 小米辣晓筱家29287 983 -

#打工人的健康餐#补气养颜的元气汤水~苹果黄芪水
黄芪 红枣 苹果 枸杞 冰糖(可不加)JUJURAI25022 783 -

快手美味#油焖笋
春笋 “太太乐原味鲜”头道生抽酱油太太乐鲜味厨房6020 201
















